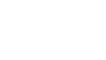睡美宁

恶呀,你来作我的善吧。
——弥尔顿《失乐园》
诗国的顽童俦里,兰波整个儿任性。拜伦狂放而文字守格,海涅发乎捣蛋而止于俏皮,马雅可夫斯基本质蛮憨,叶遂宁,被惯坏了的农家子。读其他人的诗,或幕、或怅、或和鸣、或嗔嗤,读罢也就过去,至今仍留三数耿耿于怀,对之廓然若有所付者,马雅可夫斯基、叶遂宁、兰波。亦可说诗天彗星这三颗星最熠耀得惨烈,被一己天才所误导的诗人,这种瑰琦的禀赋包括了韶美的形体,霎时间里里外外都是诗,而欺侮凌虐他们的,说起来是时代际遇,其实使他们逢凶不能化吉的却是他们刚愎的心——从三位中选一位,任何一位,或许就可以析示他们与生俱来的共性(可怜的永恒的共性),兰波的一百周年忌辰将临(Arthur Rimbaud,卒于一八九一年十一月十日),欲说兰波,总觉得宜说他的一部散文诗集,《灵光录》(Illuminations),尤其是集中五分之一的偏什。
诗是严装,散文便是便装,便装便率性惬意,是波尔莱尔开的风气吧,马拉美宁是散文诗写来比诗欲益绵妍,但兰波是不凑热闹的人,他是天生散文诗性格,叫他不写散文诗也不行,写了两集散文诗还是不行,他要散、强梁迅疾地散完他的生命。
诗人——卓荦通灵,崇高的博识,语言的炼金术。
兰波对“诗人”的名义所作的诠释是中肯的,也快说全了。诗人是实体世界上的精魂,他的诗是灵界消息,实体与纯灵难于沟通,诗人假借韵形塑造意象,使“灵”可闻可见与人亲昵,启人悟思已成欢喜。童心非即诗心,诗人具种种识,其博博在识,博学事小博识体大,学乃知,识乃觉,虽然兰波自己说的是“无比崇高的博学的科学家”,这可以解作他词未达意。(没有见过通灵的科学家,也没见过“科学诗”或“诗科学”)任何艺术都宿命地有着自始至终的技巧性,技巧出错,一上来就完,“诗”是文字的构成,甚至是非语言的非歌唱的,唯有非歌唱非语言才能一片神行,升华到诗的极峰。兰波所称的“语言的炼金术”,如果说作“语言的魔术”或者更广其义,回答“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”易,“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诗人”是更艰深的经院课题,诗的起点和定点倚仗文字的符号魔术,诗人要推辞魔术家的称号必致桂冠堕地。
就这样算水落石出,兰波的本意是:
诗人通灵,淹博,神乎其技。
兰波自己却正苦于与灵界乍畅乍塞,风尘仆仆的一生,尽啮而不及反皱,就此鲠噎住了,搁笔即成绝笔,在此之前,他对付文词用的是悖论、逆说、诡辩,掊乱感觉、意识,诚然激起诸般景观,每当收拾不起来时,状态难免狼抗乖张,不了了之到底是不了。若要说综合芳香、乐音、彩色,这样想想确是快意的(戈蒂耶也想呀,鲜花黄金大理石,何尝如意综合过来)。兰波又说“把思想与思想接通,以引出思想”,他是去践约的,而启动的思想大半是感觉,引出来的不可能是思想,仍然至多是感觉,一引再引,局面就凋疲不堪——何况在诗的王国中,恐怕没有思想家的坐处,因为思想家向来是拒诗人于理想国国门之外的。
兰波惯用的可不是“二律背反”性质的对参,他以字面对峙形相对比,来营造新感觉新境界,容易流于粗疏,满足于表面效应——也许正是这些想法手法,窒碍了上通灵界,诚则灵,不诚呢。即使是二律反反,亦不可能借作诗的方法论,二律背反与其说触及“真理”,不如说触及“极端”,使人明悉处于无处不在的“极端”之间,随时可以碰壁,而兰波的绝望,原因归诸自身,他却以为世界使他绝望,于是缠夹了二十余年,假如他寿长,只会更凄惶,诗人在有诗可写时犹煎熬若此,无诗堪写而一天天一秒秒地活着,那是什么日子,历来的大诗人蒙主召归,在乐园的浓荫下还是写诗,源源不断直到永远,否则乐园成了苦圃。
凡“xx主义”,或是词不达意,或是以词害意,象征主义和唯美主义同样是言过其实,实又不能过其言,这样起手就失误,咎由自取得没名堂。唯美,象征……皆为隐私,谜底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到谜面之前。还是很早兰波就自诉找到了他精神迷乱的性质,且是神圣的,这样,性质既然肯定,就免了他再寻找,至此真的迷乱不可解了。作为一个秉持怀疑精神的智者,他太轻信,怀疑的可知性,是从自身出发,遍及万象,又回返自身,而兰波并未回返。
酒神、酒鬼,不仅相异,正是相叛,酒神与日神并立映辉,酒鬼倒毙日光下亦非新事。兰波自道的“精神迷乱的神圣性质”,按当时说,是“实在的性质”,于百年之后的今日言,是“广泛的性质”,而有人将此两种性质论作“兰波文字的深远影响”,那是泛泛不求甚解,现代诗的模糊颠倒荒谬的普遍调门,非十九世纪象征主义之功之过,可惊叹的是现代诗风的开始,竟是如此之早,兰波的作为,竟是如此之霸,如此之绝。近代艺术的瘴岚戾气,原来发端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,世界还未曾经过两次大战,人性已起了大豁裂,两次大战无疑是人性的致命重创,反过来说,如果人性的内因不变,或者承受得起外界物质暴力亦可未知。
兰波的文学生涯短促得无需分早期晚期,说他所有作品是七昼夜写成的也可以(诗六十余首,散文诗两集,短简零札若干),《地狱之一季》有所隐射,太私人性,费力、明明事倍功半,凡审知他与魏尔伦的一段公案者,总能诊断此集的情绪化的弊病。诚如梵莱利所言,“梦与艺术正相反”,《地狱第一季》是出梦,实录的豪夺的梦也是梦,侧写的巧取的梦也仍是梦,故此集难作艺术观。要追踪兰波,便得闯入《彩色版画集》,别人为兰波编的散文诗集。
《灵光录》(Illuminations),一个迷宫,苦了近百年来对兰波有兴趣的人,读者犹可临门却步,或中途抽身,而以研究兰波作品为事业的教授学者,如安托万•阿达姆、C•夏德维克、苏珊•贝多纳、蒂博代……那就真是把《彩色版画集》当作神学、气象学、水学、地里来考辩,工程浩繁,可见世界待兰波不薄,比较下,是茨•托多罗夫的观点和方法较为剔透沉稳,到底也不能从没有太多的东西中说出太多的东西来——兰波常会未问先答,他置很多门,叫别人莫叩门,他却在门内坐等:
不必重视我的智慧
正如混沌之可鄙弃
和你虚无相比
我的狂妄又算怎么
妙就妙在(不妙就不妙在)兰波这番自白并非真是冲谦练达,而是挑逗,赌气。他们(兰波、马雅可夫斯基、叶遂宁)其实还算不是被宠,却像被娇宠了的孩子,彗星型的诗人都这样,自恋,自恋狂,犯自恋的情杀案。《彩色版画集》是率性之作,读难,译更难,退远了看,不失其为寒空耀目的孤星,近而逼视,缭乱纠结不可方物——兰波是谁,什么才是兰波,正在这个集子中,即使不得答复,也会有阵阵回声。这些散文诗,但是目诵是无济的,唯有用笔来撩拨它们,那就不再是移译,亦无论窜改,突然表明有人曾以此项款式阅览《彩色版画集》中的一些篇章。
用以上的方式解读兰波的散文诗动机是叵测而可测的——现代和后现代的诗人群中,颇不乏夸言如何如何一往无前者,那么,请看看兰波,一百多年前写成了的是什么,兰波超越了时代,时代不过是历史的枝节对于不良的时代,超越了又如何呢。对世界发声,世界使一个没有回音的空谷,面壁与面世何异,可以观可以兴可以悦可以怨的还是“人”,单个的人,墓志铭似的看着他,诗人兰波。 他出生于夏尔维勒,属阿登省,法兰西快要与比利时接壤的那里,地里环境对一位诗人真有影响吗,多半可说没有,生理遗传呢,连常人的性格也不决定于种族血统,何况特立独行的畸零者。兰波之父服役于军旅,母亲是农家女。传说兰波刚出世,助产护士去端了温水来要给他洗澡,却见他已从床上爬下,爬到房门口,双目圆睁……情景诚是非常之兰波,即使为了形容一个天才而捏造了这个画面,也捏造得好,兰波一诞生就十足兰波了,这点事迹装在别的诗人身上是不合适的。
在夏尔维勒市立中学,兰波受诲于乔治•伊藏巴尔,这位修辞学教师激赏兰波的异秉,爱得忧心忡忡,太不安分的学生将来与世界势难和睦,世界从不谦让,兰波又不知谦让为何物。
象征主义又象征什么。人们习惯闲谈魏尔伦与兰波的聚散,那是他两人的遭遇,何须第三者置喙置评,魏尔伦初见兰波,惊愕于他还是个孩子,于是去布鲁塞尔(一八七二年七月),去伦敦(九月),兰波返乡(十二月),越明年,又在伦敦相会(二月),又去法国(四月),又去伦敦(五月),他俩在伦敦过的是流浪者的生活,爱是手掌恨是手背,拉住这手的是死神,七月十日,在布鲁塞尔,魏尔伦开枪了,开了不止一枪,存心致兰波于死,实际伤了兰波的右腕,住入圣约翰医院,涉讼不可免,一丝残剩的爱念使兰波撤回起诉,很可能兰波是用左手写《地狱之一季》道德,这是一本不智的诗集,缪斯女神从来不兼复仇女神,艺术是不大受理太私的私事的,兰波自费印了五百册,只取走样书六册,以赠朋(单人旁齐),其余就弃而不顾,欠款也赖付,十足浪子作风,他继离魏尔伦之后,便离文学,一八七四年去伦敦,从兹永别诗神。
一八七五年,去德国斯图加特,经瑞士越阿尔卑斯山到米兰,被里窝那法国领事馆扣押,遣返马赛。
一八七六年去维也纳,被奥地利警方驱逐出境,身无分文,徒步从德国南方到法国,在布鲁塞尔应荷兰外籍军团招募,航海抵爪哇,进入内地——他不喜欢,潜逃,作为苏格兰船上水手,回爱尔兰,经巴黎转夏尔维勒,该是浪子回家?不会的。他不属于家,不属于法国,不属于世界,这都不悲哀,悲哀的有:他不属于自己。
一八七七年——德国不来梅,瑞典斯德哥尔摩,丹麦哥本哈根,意大利罗马。
一八七八年——汉堡,瑞士,地中海,塞浦路斯。
兰波吃什么喝什么,穿戴什么,都来不及想象,只知他一直在动,体格似乎是强健的,脸很英俊,五官与马雅可夫极为相似,而他的行径,像是中了魔法?受了诅咒?如此惶惶不安于任何一种现状。一八八〇年,他在塞浦路斯某工地做领班,因待遇不佳离而赴亚丁,自是年七月始在亚丁一家法国人经营的商行供职,与皮货和咖啡周旋,十二月被商行派往埃塞俄比亚哈拉尔地方分行做理事。至此,他累了?他悟了?他完全失去自己了?怎么一个人在哈拉尔停留十年,如果这十年重又写作,尽管是业余消闲的写作,那会是另一个兰波,或可说是真正的兰波,但他的飘游是无目的无志趣的,为艺术而艺术到头来是艺术,为飘游而飘游到头来什么也不是。希腊神话是一大部无微不至的神话,凡想得到的,都有一位或数位神在那里主宰,天、地、海、风、日、月、酒、爱、战争、文艺、收获、贸易、狩猎……都有神,唯独没有一尊司流浪的神,“神明保佑强者”,神明不佑护流浪者。
兰波薄于名利观念?单于情爱欲望?对自己的诗漠不关心,人在非洲,诗的声誉在巴黎蒸蒸日上,如果天使把塞纳河畔的声誉带到哈拉尔,兰波也置若罔闻——这种男子是有的,这种男子的第一特征是矫健,其次是昳丽,再次是多智而寡情,若说他的心灵亦有所交替变换,那是冷淡——冷酷——冷漠......而他的状貌举止却吸引人的好奇、审美、求知,这种男子是凛冽的自恋者,又不懂如何个恋法,终究沦为透辟的自弃。这种男子一直会有的,在《圣经》中就有,名字叫该隐,后来的哈姆雷特、曼弗雷特,乃至俄罗斯的皮巧林……都是自甘掩脸沉没的超人,终生骚动不安,上下求索,凡得到的都说作他所勿欲得到的,于是信手抛掷,取一种概不在怀的轩昂态度,宠坏了孩子是无救的,不宠而像宠坏了的孩子更无救,他们早熟,注定没有晚成可言,然而他们阳刚、雄媚,望之恰如诸君。
兰波说:
“精神上的搏斗和人间的战争一样暴烈。”
兰波有无参与人间战争,那不重要,在精神上,他为时不长的阅历,经历何种“搏斗”?与什么强敌抗衡?希腊的?希伯来的?都不是他的亲仇,像兰波那样的人,同情悯恤着无庸议,让他去,看他走过,看他折回,又启程——邻家漂亮的坏男孩,当他睡在草推上,胸脯均匀起伏,那时,头上真像有一片虹彩光环,可怜的不要人可怜的孩子,同够了尘也和不了光的诗人。
世界小,人类微末,流浪不是专业,骄狂傲岸,倒是把生命认真当作一回事了,单凭双腿走来走去,以取“无比崇高的博识”,怎会是“通灵者”?“语言的炼金术”,当然是个比喻,这句话本身嫌惫赖:炼金术士用“智者之石”并未无中生有得到过黄金,中世纪的炼金术启迪了后世的化学实验,而炼金术士在当时不过是执迷不悟的巫师,或能欺人却不能自欺的江湖骗子。如果说借兰波的诗,可以感知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法国生活气氛,那又是唯物史观文评家的“反映论”作祟,以兰波的自私、自负,他才不在乎一个法国一个世纪一个年代。兰波写过《醉舟》,他便是醉了的舟子,舟也醉了,可惜人饮和舟浸的都不是狄奥尼索斯的葡萄所酿的醇醴。要么从来不与艺术结缘,既结,再绝之,难免要得到报应,这样的事例时常可以看到,不过没像兰波那么彰显(也有比兰波更彰显的)。兰波最后的死因也象征性的,没钱雇车搭船,他一步步走,一八九一年二月,右膝肿痛,四月,抬回亚丁,五月抵马赛入医院,不得不截肢,八月,肿瘤扩散,十一月十日,亡。
马拉美重“句法”,兰波重“词汇”,亦有说马拉美是夏娃,兰波是亚当,他以虐待文字为乐,他以碎块来炫耀他可能拥有的形体。令人惊讶的是马拉美曲径通幽,从此没见有人寻探,兰波的驿道却被众庶走大了,走得泥泞四溅。令人更讶异的是这些云云后生并非知道那是发迹于兰波的路(兰波也以为自己开拓自己的行迈,别家休想踏得上)——真是奇怪,其实一点也不奇怪,“诗”的命运,相同于所有玛与蛾摩拉的命运。再一百年后,再有谁悼念兰波,果若用兰波的“词汇”来作述兰波,那将是沙呜海立溃不成兰波了。
他自诏“全部感官按部就班地班地失常”,这个“兰波模式”,实证在生活上,一路颠沛流离,都只是忍受而难论享受,要么他是个以忍受为享受的人,又不像,宁是像以享受为忍受的人哩。
(“常”是大宿命,无由失,或者可以“反常”,可以“非常”,反常非常企求更高更新的“常”——“失常”则尚未意识到有更高更新的“常”的存在可能,此时贸然否定“常”,亦就自绝于“反常—非常”的祝福)
血性的而非灵性的兰波。伊卡洛斯搏风直上,逼近太阳,以致灼融羽蜡,失翅陨灭。兰波的天才模式是贴地横飞的伊卡洛斯。
选自《即兴判断》/木心/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
今天睡美宁的内容先分享到这里了,读完本文后,是否找到相关的答案,想了解更多,请关注www.yujiaowang.com鱼胶网站。版权声明: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,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。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,不拥有所有权,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/违法违规的内容, 请发送邮件至 294298164@qq.com 举报,一经查实,本站将立刻删除。